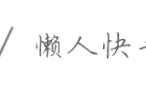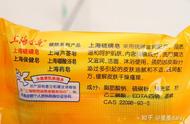大同的刀削面,浇头无论荤素,一般都会覆在面上端将上来。在这个时候,浇头就成了削面的门面儿,荤臊子肉香十足,素臊子厚味绵长,吃面的人就夸赞,好面---好的浇头,往往是各种面条画龙点睛般的存在。

苏州的头汤面,功夫下在两个方面。当地有名的枫镇大肉面,先要吊汤。一锅好汤,用鸡鸭骨、黄鳝骨、螺蛳来吊制,中间还要加入酒糟,来增加汤味的醇香。配着面一起上桌的浇头,是一条儿慢工焖出来的白净五花肉,每条儿一两二重,卧在苗条的细面上,压舱石一样。

“苏面”另一种浇头,与北京炸酱面有一些相似。素面配着浇头端上来,或者长鱼(鳝鱼),或者三虾(虾籽、虾脑、虾仁),或者卤鸭,或者焖肉,由客人自由支配。嗜酒的人们,先用浇头下酒,浅斟慢饮,边喝边琢磨浇头的滋味。酒瘾解得差不多了,把面碗拖过来,将面条挑入浇头碗里,称作“过桥”。这样一种吃法,浇头既是酒菜,也是面码儿。
国人吃面的历史源远流长,浇头也“跟”着面,不知道走过多少个春夏秋冬。

随便翻一翻宋人留下的笔记,诸如三鲜面、丝鸡面、炒鸡面、卷鱼面、笋辣面、鱼桐皮面、素骨头面等等,扑面而来。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讲,“面有浇头,以长鱼、鸡、猪为三鲜。”
这么多的面,如果把它们名称里的“面”字暂时去掉,那么,留下来的恰恰就是当时“流行”于我们老祖宗饭碗里的各样浇头!假如再细细考究,当时的这些浇头,与如今的浇头,并不因为岁月更替而断了联系。
名著里的“浇头”
《红楼梦》第六十一回,迎春的丫头司棋,冲着厨娘柳嫂子发了一通大火,起因就和浇头有关。司棋打发小丫头莲花儿,通知厨房要一碗蒸蛋。柳嫂子推三阻四,并不买账,最后惹得脾性刚烈的司棋,带着一帮子小丫头,居然砸了柳嫂子的厨房。柳厨娘不肯做蒸蛋的理由是,“通共留下这几个(鸡蛋),预备菜上的飘马儿。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遇急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