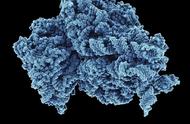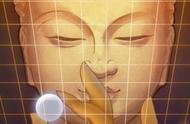有一位古蔺县领导曾戏称江门是古蔺第三招待所——那时古蔺县委与县政府各有一招待所。那些配了小车的部门与率先发富的私营老板,都是江门荤豆花的铁杆粉丝。一来二去,那场镇边“曾德华荤豆花”餐馆老板娘居然熟悉到这样招呼, “王局长来了呀” “赵*来了呀” “汪经理来了呀”“罗大老板来了呀”——“曾德华荤豆花”是江门荤豆花最早创建者之一,味道自是资格正宗。大纳路开通后,又率先从逼促的场镇搬到大纳路经过的江门峡口桥头,修了门面高大的餐馆,门口大坝子又好停车,还免费冲洗。主打荤豆花之外,又增添了苦芛烧黄辣丁、大竹芛烧鸡、爆炒猪肝猪腰猪肚、山野葱拌侧耳根等特色菜品,很对这些不差钱的主顾味口。

顺便一说,“曾德华荤豆花”红火几年后,“牟氏荤豆花”在接近江门峡出口处又异军突起,其味道也好的不要不要的。加之此处举目野山野水,又得几棵黄桷树掩映,说不出的优雅清宁,即便三伏天,也有一番清爽。有趣的是,与“曾德华荤豆花”一样,也由老板娘主厨,一个快人快语,一个白晰温婉,时人誉之“江门峡双娇”。
二
当年江门因荤豆花而掀起的“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热闹景象,一个就读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古蔺后生,曾有过这样的意识流诗意发散——那是1989年初春,他站在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一书中说的“横石中流,束水如门”江门峡,看着青岩山一山如火桃花、春风中青青翠竹、唱着山歌犁田的农家汉子,听着身边汽车喇叭声、豆花作坊“依呀”石磨声、永宁河中流水声,他的思维进入了幻听幻视状态——青嫩春芛钻出泥土,木姜树吐出小白花,油菜花黄了路边也黄了山上,黑毛猪在圈里嘻哈打笑;夏天灼热的阳光下,蕃茄涨红,辣椒光合作用出辣素;黄豆在金秋炸裂,鱼在金色的水中跳跃,青菜在山土中吮吸冬天霜雪……这些千年百年生于斯长于斯的精灵,响应荤豆花吹奏的集结号,从云端上跳下来,跳入石磨,跃进大铁锅,登上餐桌,香气飘向南来北往人肠胃,汇入大车小车喇叭声中,俨然就是一曲天人合一的春天交响乐……他后来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但自嘲诗作脱不了荤豆花气味。

稍逊风*的是,这个赤水河畔大山中的古蔺学子专业不是历史。在他天马行空的意识流中,少了对江门荤豆花起根发角的探寻一一关于江门荤豆花的来历,有多种说法。郎酒掌门彭追远先生从“沈豆花”老板沈老妈子那里听说的来龙去脉,应该比较靠谱。整个90年代,彭厂长时常奔波大江南北,来回大多要在江门刹一脚,进场镇吃荤豆花,并只认“沈豆花”。一次就问起荤豆花来历。沈老妈子说,“文革”刚结束时经济还不发达,客车途中吃饭大多是在叙永县城或是纳溪上马镇。她经营的小饭馆,主卖几角钱一碗的素豆花,还有用回锅肉料切片与盐酸菜、豆芽、叶子菜一锅煮的“一锅熟”,外加小炒。客人大多是过往货车司机。一个赶场天下午,来了同行两车,司机要了“一锅熟”,吃了不够喊加肉。但肉已卖完。司机见大铁锅中还有几砣豆花,就叫放进肉汤煮吃。一筷子进口,大呼“安逸!”之后再来时,直接叫“一锅熟”里加豆花,还将这吃法向同行推荐。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就有了名声在外。沈老妈子又不断加以改进,将回锅肉料改为瘦肉片,还加入鲜蘑菇、蕃茄与苦芛,油酥糍粑辣椒蘸水中又加入木姜油,于是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其中,一些货车司机也提出了不少建议,比如,就建议用“荤豆花”作菜名,区别于他处素豆花——历史的真实可能就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末期,江门一个经营小餐馆的普通妇女,与过往货车司机共同创作了川南餐饮奇品“江门荤豆花”。这就像许多长篇小说开篇第一自然段都很平实一样。其实,这也证明了一个伟大论断,有些历史肯定是人民群众亲自创造的。

插说几句题外话,那沈老妈子一提谈起彭厂长,就满脸敬服——没名酒大厂长架子,说话平和近人。吃又俭省,是个懂得过日子的人,断不点鸡鱼,说到江门就是来吃荤豆花的。如果只司机和他,就点一个荤豆花,一个小菜;如果同行五六人,就要一大盆荤豆花,一个素菜,一个凉拌菜,加炒一个回锅肉,并要大家把汤也喝完,说吃了不可惜,吃不完浪费可惜,糟蹋吃食天打五雷轰。有一次彭厂长听她说过几天要生,还送了两瓶郎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