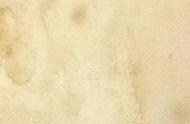”“

”“

”则为“斑”“班”的分化字,
“
”为“鲗”的异体字。
考释内容将有助于今人校订整理中医古籍。中医古籍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了中华中医药学的理、法、方、药等,是中医学术传承的主要载体,也是当今中医药学“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源头活水。中医古籍作为一种实用文献,存储了大量的俗字,其中不乏未被历代字书所收录的俗字,这些俗字成为当今中医古籍阅读、整理和利用的障碍。王永炎(2018)指出:“中医药学重视发掘传承,必须对重要的古医籍进行系统化、规范化、多方位、高层次的诠释研究,积学以启真,述学以为道,使中医古籍为今人所理解、所应用。”中医古籍俗字研究即有助于中医典籍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李从明《本草纲目词句研究》(1996)、沈澍农《中医古籍用字研究》(2007)等专著,以及范登脉(2000)、孙孝忠(2003)、刘敬林(2011),以及马乾(2021,2022)、周艳红(2021,2022)等对《本草纲目》、唐宋时期手写中医文献、日藏中医文献等文献中的疑难俗字进行了考辨,纠正了今人点校整理本中的部分疏误。
本文选取宋以来中医古籍中从虫的疑难俗字6组、8个,对其音义信息、形体源流等做了梳理,校正了今人点校整理的部分失误,并对《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字书的修订提出了若干意见。
1.
金张从正《儒门事亲》卷十五《疮疡痈肿》:“烧汤火方:多年庙上与走兽为末,小油调,涂烧汤火疮,立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V745P335①)、
元汪汝懋《山居四要》卷三《卫生之要·新增诸证杂方一类》:“治汤烧:用多年庙上与走兽为末,水调涂烧疮处,立效。”(《寿养丛书》本)
按,,《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未收。《儒门事亲》校注者多照本抄录而不注,徐江雁、徐振国主编《张子和医学全书》注曰:“,虫名,即马陆。”(2015:169)李经纬点校本《寿养丛书全集》传抄作“物”(1997:123)。
今考,“庙上”即“螭吻”,“”为“螭吻”之“吻”改换义符的分化字。螭吻,是古代宫殿屋脊正脊两端的一种饰物,多为龙头鱼身状;其初作鸱尾之形,后来式样改变,折而向上似张口吞脊,因名鸱吻。“螭吻”文献传抄作“螭”,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二:“古诸器物异名。……螭,其形似兽,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墨海金壶本)从《儒门事亲》《山居四要》语境看,此处当为“螭吻”,徐江雁、徐振国等解释为“马陆”不当,《寿养丛书全集》传抄作“物”亦误。
螭属于兽类,故文献中“螭吻”“螭”又称“兽吻”“兽”。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二:“兽,其形似狮子,性好食阴邪,故立门环上。”(墨海金壶本)“兽”即“兽吻”,清刘灿《支雅》卷下《释物·山中物名》:“兽吻,立于门环,形似狮,性好食阴邪也。”(清道光刻本)此处的“”即“吻”的分化字。“庙上与走兽”,明清中医古籍多传承作“庙上兽头”,如明张时彻《急救良方》卷二《杂方》:“治汤盪火烧:用多年庙上兽头为末,小油调傅之,效。”(明嘉靖刻本)此兽头即为“螭吻”。
值得注意的,已编码字“”为越南喃字,壮语、越南语中将山蚂蟥称之为昆,故王宏源《康熙字典(增订版)》据中日韩越统一字符集(CJK)收录“”字(2015:1452)。《中华字海》《汉语大字典》等均未收录此字,实际上汉文古籍中“”字多见,《中华字海》《汉语大字典》修订时可据汉文古籍增收“”字。
2.
清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卷十七《下品药》:“水蛭:味咸苦,入足厥阴经,功专破血行伤。得蜚,治畜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V783P934)
按,“”,《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未收,王宏源《康熙字典》(增订版)据中日韩越统一字符集(CJK)收录“”字(2015:1461),乃越南喃字。今考,汉文文献中,“”与“虻”“䖟”“蝱”为异体字关系。“蜚”即“蜚䖟”,中医学认为水蛭搭配蜚可以消除淤血,这种治疗方法本于《伤寒论》。汉张仲景《伤寒论》卷五《辨阳明脉证并治》:
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2004:134)
该书卷三《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抵当汤方”条曰:
水蛭(三十个,熬。味咸,苦寒) 蝱虫(三十个,熬。去趐足。味苦,微寒) 桃人②(二十个,去皮尖。味苦甘,平) 大黄(三两,酒浸。味苦寒)。(苦走血,咸胜血,蝱虫、水蛭之咸苦,以除畜血。甘缓结,苦泄热,桃人、大黄之苦,以下结热)右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2004:95)
该书卷三又曰: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抵当丸方:水蛭(二十个。味咸,苦寒) 蝱虫(二十五个。味苦,微寒)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大黄(三两)。右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2004:95)
以水蛭、蝱虫、桃仁、大黄治疗体内淤血,此当为较早的记载。宋以后医家对于抵当方、抵当丸的药理进行了阐释。如宋韩祗和《伤寒微旨》卷下《畜血证篇》:
凡治畜血证,抵当汤丸方中皆用蝱虫、水蛭及桃仁之类,尽是破血药,若非此药,则不能下之。(清《珠丛别录》本)
又金成无已《伤寒明理论》“抵当汤方”条下曰:
人之所有者,气与血也。气为阳,气滞而不行者,则易散,以阳病易治故也。血为阴,血畜而不行者则难散,以阴病难治故也。血畜于下,非大毒駃剂,则不能抵当其甚邪,故治畜血曰抵当汤。水蛭味咸苦、微寒。《内经》曰:咸胜血。血畜于下,胜血者必以咸为主,故以水蛭为君。䖟虫味苦、微寒。苦走血,血结不行。破血者必以苦为助,是以䖟虫为臣……(宛委别藏本)
清杨时泰《本草述钩元》卷二十七《虫部》“水蛭”条:
水蛭以蠕动啖血之物,治血之蓄而不行者,与虻虫功用相似,故仲景方往往相辅而行。自有抵当汤丸,治伤寒畜血,而后来治畜血诸证不因于伤寒者,亦不能外此二味,只随证以为加减而已。(2009:757)
从医方源流来看,“蜚”即“蜚虻(䖟蝱)”无疑,“”即为“虻䖟”替换声符而构造的异体字。
以蝱虫治疗淤血较早见于《淮南子》。汉刘安《淮南子·说山训》曰:“狸头愈鼠,鸡头已瘘,䖟散积血,斫木愈龋,此类之推者也。”此方为中医学所承袭,故中医学家多认为蜚䖟有活血的功能,如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一《虫之三·蜚䖟》:“按刘河间云:䖟食血而治血,因其性而为用也。成无己云:苦走血,血结不行者,以苦攻之。故治畜血用䖟虫,乃肝经血分药也。”此亦可证“蜚”即“蜚虻(䖟蝱)”无疑。
汉文文献中“”又为“莣③”之易旁分化字,字又替换声符作“”,或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