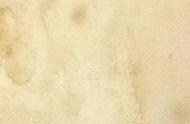”等。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九:“譬若空桑之流,弗知,大椿之年,蟪蛄何觉。”(清道光刻本)“”即“莣”,今本《淮南子·齐俗》:“水虿为莣。”许慎注:“蜻蛉也。”王引之《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十一》“莣”条考“”为“蟌”之误、“莣(

)”为“䓗”字之误,“䓗”为“蔥”的俗写。(清道光十二年本)杨宝忠疑“蔥(䓗莣)”为“蟌”的直音用字。(2018:393)后世不知,遂误以“莣”为蜻蜓的别名,今钦州白话称蜻蜓为“蝞”“䘃蝞”,其则又为“莣”的俗音。“”又改变声符作“”,见于明刘胤昌《刘氏类山》卷四《虫鱼》“水䘍为”、清刘灿《续广雅》卷下《释虫》“,蜻蛉也”等;“”又讹作“”,见于《渊鉴类函》卷四百四十六《虫豸部》“蜻蜓”条下引《淮南子》:“水虿为(矛)(务),蜻蜓也。”“”即“”,“巳”“亡”形近而误。
综上,中医文献中“蜚”之“”乃“虻”“䖟”“蝱”替换声符构造的异体字,其与《淮南子》中“”之“”为同形字关系。“”又为越南字喃,壮语、越南语将眼镜蛇称之为“

虎”(王宏源,2015:1461)。这样看来,汉字文化圈中“”为一形三字的同形字。
3.䖾
宋佚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卷二《食忌论》“小儿不可食黍米、鸡肉、胡瓜,令儿腹中生虫”条下注:“《经验方》云:小儿未断乳食鸡肉,令儿腹生䖾虫。”(《文渊阁四库全书》V741P72)
按,“䖾”,《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未收。今人整理简体字本《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多作“蛔”,繁体字本则多作“蚘”。王宏源《康熙字典(增订本)》认为其为讹字,并指出重订曹氏医学大成本作“蚘”。(2015:1461)从形体源流来看,“䖾”当为“蚘”字之讹。
婴儿吃鸡肉会生蛔虫的说法较早见《齐民要术》。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六《养鸡》:“《养生论》曰:鸡肉不可食,小儿食,令生蚘虫,又令体消瘦。”④(1982:334)中医药文献多承袭此类观点,如唐苏敬《新修本草》卷第十五:“小儿食鸡肉,好生蚘虫。”(日本抄本)南朝梁陶弘景则将“小儿”的年龄限定在五岁以下,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卷十九《禽部三品·诸鸡》“简误”:“弘景云:小儿五岁以下食鸡生蛔虫。”(2011:267)相似内容在唐宋以来养生类文献中多见,如宋周守中《养生类纂》卷八《人事部·小儿》:“小儿食鸡肉生蚘虫(《本草》。又《婴童宝鉴集》云:未二岁勿食鸡肉,子腹中生虫。)”(明刻本)
中医学认为,不但婴儿不适宜吃鸡肉,孕妇也不宜吃鸡肉。如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妇人方·养胎》:“论曰:儿在胎,日月未满,阴阳未备,腑脏骨节皆未成足,故自初迄于将产,饮食居处皆有禁忌……妊娠食鸡肉糯米,令子多寸白虫。”(2011:22)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卷三十三《养胎法并禁忌一十三首》同载:“妊娠食鸡肉、糯米,令子多寸白虫。”(2011:591)唐昝殷《经效产宝》卷上《妊娠食诸物忌方论》:“食鸡肉与糯米共食,令子生白虫。”(2011:3)蛔虫为白色或米黄色,此处的“白虫”亦当指蛔虫。
由此可见《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载“䖾”为“蚘”之变无疑,部件“尤”“完”形近而误。《字海网》载“蚘”的异体字作“”,其右部皆与“完”即形近,“”或即“蚘”书写变异作“䖾”的中间形体。王宏源《康熙字典》(增订版)注“䖾”为“讹字”(2015:1461)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蚘”文献中又讹作“”。宋杨士瀛《仁斋直指》卷六《脾胃》“和胃证治”条下:“乌梅丸治胃冷,虫攻心痛,呕吐,四肢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句又见于该书卷二十五《诸方》“诸虫方论”段,字即作“蚘”。“尤”“冘”形近混同,相似情况又见于“

”书写变异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