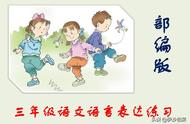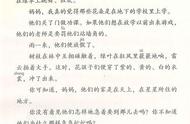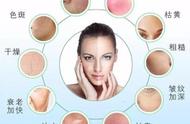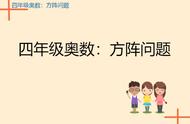——这是一篇散文诗,兼有诗歌与散文的特点,具有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美,但又没有分行和押韵。课文以“花的学校”为题,花是娇嫩的、美丽的象征,有如孩子般纯洁,他们在“地下的学校”,就像泥土里即将破土的苗,渴望外面精彩的世界。课文以儿童的视角描绘了一群活泼、天真、渴望自由的花孩子,通过丰富的想象,把孩子和妈妈之间的感情表现得自然深厚。——
看看这一段教辅书中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他们在‘地下的学校’,就像泥土里即将破土的苗,渴望外面精彩的世界”。
这里所说的想从地下的学校破土而出,是渴望外面精彩的世界吗?其实课文中说的明白,是他们讨厌在学校里的压抑氛围,想早点回家。教辅读物说的遮遮掩掩,明明原诗中表达了非常强烈的对学校的反感,你现在非要把它拉上“渴望外面的精彩的世界”,难道不上学校,逃离学校,就是渴望外面的精彩的世界吗?这的确很符合部编版教科书的“人性彰显”的主题,但是这种彰显出孩子的自由意志与人性释放,是否违背了学校设立的目的,以及老师在课堂上教育孩子们的动机?

用“人性彰显”的理由,来反向地制造出一个惩罚学生的对立面,并非是这一篇课文中独有的意境。
在小学五年级下册的《童年的发现》一文的最后一句中,小学生们将继续学到一个抨击老师束缚与压制的愤怒的控诉:我“被轰出教室,站在外面,我倒想出了一条自我安慰的理由,我明白了——世界上的重大发现,有时还会给人带来被驱逐和被迫害的风险。”直接把老师设定成为一个“迫害学生”的邪恶力量。
这种邪恶力量的设置,与《花的学校》里的“地下的学校”里弥漫着惩罚的压抑情结的构思如出一辙,都是在激化着孩童心里对学校严格制度与学习悬梁刺股性质的抵触情绪。虽然看起来,该课文似乎目的是释放孩童的天性,实现教材的“人性彰显”的目的,但很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给孩子心里以一种不良误导,走向放纵自我、失去束缚、为所欲为的岔路。
而再深入一层地连缀起来把握一下《花的学校》里的意象,在泰戈尔的诗歌中,也不是上乘之作,反而是一种刻意的呆板的造作的败笔。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诗中描写的那些从“地下的学校”钻出地面的花孩子们会有一种美感吗?再注意一下,这些花后来上哪里去了?按照泰戈尔的想象初衷,他是想说,这些花从地上冒出来,然后扶摇直上,到了天堂,诗中我们明确看到这样的设置:“他们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
这些花孩子是直奔天上,回到他们的家里,家里有母亲。这种想象,与泰戈尔所在国家的宗教信仰有关,我们找一段教科书上对泰戈尔笔下的神性的分析:
——原来,在泰戈尔看来,宇宙万物有一个共同的主宰者,这个主宰者是一个无形无影而又无所不在的存在――“梵”,而“梵”也就是神;人们只有达到与“梵神”完全合一的境界,才会真正感到快乐和幸福。——
《花的学校》里,联合起来看,就是表现了一群花孩子,受到地下学校的压迫,借暴风雨的契机,逃了出来,然后,奔向了他们的归宿地,那个充满着母爱的天空。

再具体地想象一下,一群花,从地底下钻了出来,铺满了地上,然后,他们突然都腾空飞起,飞上了天空,他们的家。这种意象会不会有一种魔幻的怪异色彩?
中国著名诗人闻一多当年对泰戈尔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
——泰戈尔的文艺的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文学是生命的表现,便是形而上的诗也不外此例。普遍性是文学的要质而生活中的经验是最普遍的东西,所以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生命的基石上。形而上学唯其离生活远,要他成为好的文学,越发不能不用生活中的经验去表现。形而上的诗人若没有将现实好好地把捉住,他的诗人的资格恐怕要自行剥夺了。
印度的思想本是否定生活的,严格讲来,不宜于艺术的发展。……
由此我们又可以断言诗人的泰戈尔定要失败,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现实的人生的基石上。果然我们读《偈檀迦利》,《采果》,《园丁》,《新月》等等,我们仿佛寄身在一座云雾的宫阙里,那里只有时隐时现,似人非人的生物。我们初到之时,未尝不觉得新奇可喜;然而待久一点,便要感着一种可怕的孤寂,这时我们渴求的只是与我们同类的人,我们要看看人的举动,要听听人的声音,才能安心。——
根本要害,就是泰戈尔的文字里没有生活,只有抽象的带着神喻的无法实指的信条。这种东西,使得泰戈尔始终没有成为中国文学接受与学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