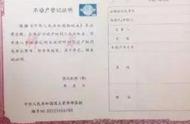“白露高山麦”。收完核桃,农人们就在白露和秋分之间的这段日子里,从深山、浅山、河谷依次开始播种冬小麦。经验告诉人们,如果过早播种,麦子在隆冬来临之前就会拔节,拔节的麦苗容易被冻死,减产和绝收的概率将大大增加,所以,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稼人,会因地因时将作物播种的时机拿捏的很到位。

临近秋分,地里的庄稼陆续成熟。山里的野猪、狗熊会如约光顾玉米地、黄豆地。特别是野猪,它们常常结伴而行,一夜之间就能让村民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为了不让即将收获的粮食毁于一旦,村民们用木头、茅草、塑料布搭起一座座“介”字形的庵棚。无论是月朗星稀的晴天,还是风雨交加的雨夜,一条狗,一堆篝火,一把手电筒,一个废弃脸盆,陪伴着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听吧,那对面的山梁上,又响起“咣-咣-咣”的敲击声,那忽明忽暗的篝火,如一双双眺望的眼睛,彻夜放射着警惕的光芒。
收玉米也不像想象中的轻松。玉米叶片宽大锋利,为了不划伤手臂,一般人们会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掰玉米时,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来来回回穿梭,苞米叶须粘得满脸都是,豆大的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那个滋味真是不好受。好不容易捱到太阳落山,但辛苦还没结束。吃过晚饭,全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边拉家常,一边剥玉米苞叶,直到更深露重、万籁俱寂,一家人才疲惫地各自散去。一觉醒来,看着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堆满高高的谷架,村人们难掩心中喜悦,连日来的疲惫也化作烟消云散。

节气不等人,掰完玉米,紧接着就该收割黄豆了。寒露一过,黄豆茎叶开始变黄,苗秆和豆荚变干,呈现出黑褐色。这时的豆荚被太阳一晒,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得抓紧时间完成收割。割黄豆时,一般都赶在太阳出来之前,早晨湿气重,豆荚不易裂开,但裤角和鞋子经常被露水浸得湿漉漉的。豆荚角上有一个硬尖,跟刺一样,收割时极易刺伤手掌,就算带上手套也得小心翼翼。接近中午时就要停下收割,赶紧装车拉回,均匀地平摊在晒场上。等吃过午饭,男女老少分成两组、相对而立、手握连枷,各自在手心轻轻唾一下,接着就是此起彼伏、铿锵有力的“哒-哒-”声,连枷在豆秸丛上交替回落,金黄的豆子在噼啪声中应声而落。地毯式的打完一遍,再将豆秸翻个身重复一次,直到豆荚与豆子全部脱离,再去杂晒干后入仓储藏。豆秸中含有丰富的粗蛋白质和粗脂肪,牲口吃了长膘快,所以一般绝不会被丢弃或用作燃料,而是晒干粉碎后作为牛羊过冬的“细粮”。

霜降过后,树叶已稀疏凋零,红彤彤的柿子挂在光秃秃的枝干上,像秋风中的一盏盏红灯笼,温暖着人们的双眼。在那个农业生产相对落后的年代,耐存储的白菜、萝卜、土豆是冬天餐桌上的“吉祥三宝”。家中的女主人将一部分蔬菜搬到提前挖好的地窖里,再留出一部分腌制成酸菜和泡菜。男人们会到山里夹些柿子回来,削皮后用绳子串连起来挂在屋檐下,经过霜*,水分挥发,果肉收缩变小,这时候取下捏成薄饼,一层层放入瓦罐中封存一个月左右,开始有洁白如雪的柿霜溢出表皮,香甜软糯的柿饼就做成了。象征着红红火火、事事如意的柿饼,常被用作哄家中小孩、招待客人的小零食和走亲访友的小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