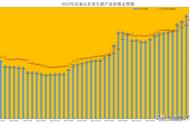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我认为北方人类最充盈的“膘”应当是讳莫如深的年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饕餮5天、7天、15天,甚至超过30天。这种囤积脂肪的过程是大名鼎鼎的秋膘无法攀比的,毕竟秋膘只是仪式感地存在了立秋那么一天!而起自腊月里*年猪开始贴的年膘,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大吃大喝后,也终于在农历二月收尾——二月二吃猪头乃是过年盛宴的最后狂欢!
据说吃猪头的习俗是因为旧时*年猪后,猪头摆供。出了正月,猪肉耗尽,只余猪头。届时“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的中国北方,天气转暖且缺乏制冷设备保鲜,猪头若再不吃就可能要坏掉,故此衍生出二月二吃猪头的习俗。不过我的记忆里,二月二吃猪头已经是一种旧俗应景。作为城里长大的孩子,我记得除非个别年景有农村亲属特意在*年猪后,把头蹄下水当年礼送给我家,更多时候,二月二的猪头都是家里特意花钱去买的。
在九十年代中期,我的爷爷奶奶还健在的时候,二月二吃猪头是马虎不得的。尽管那时街市上已经有一些卖熟食猪头的店铺、摊床,因为节俭观念及饮食习惯等缘故,不仅我家,吉林城好多住户还是不怕麻烦,坚持购生猪头自己烹饪。
买猪头要越肥大越好,没膘的不香!我隐约记得家里有西关黄旗屯肉联厂的关系,总能买回比较满意的。可比起大快朵颐着吃肉,拾掇大个儿猪头的确是一项比较麻烦的工作。首先要在火上燎猪头上的长毛,然后用烧红的炉钩子烫去残存的毛茬,接着就用开水烫、用刀刮以去污除黑,反复数次才能将猪头处理干净。为了缓解燎猪毛时四溢的焦臭味对节日氛围的影响,我家的长辈们此时会纵容孩子淘气捣乱。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就爱拿着炉钩子在长辈身前身后乱窜,对着那猪头比划程咬金的三板斧:劈脑门、挖眼仁、掏耳朵。边比划边喊出招数,浑然不顾那猪头的亡魂有何感受!

猪金钱,就是猪的上颚,川菜里叫猪天梯
收拾干净的猪头割舌剃耳,有时还会把个头过大的猪头劈成两半。因嫌弃猪脑子太腥(始终未得处理要领),这部分往往被我家扔掉。处理好的猪头冷水下锅,加上调料,文火开烀。烀肉的过程比较久,而对渴望吃到肉的孩子来说,那时间仿佛更加漫长。
在最后烹入白酒去腥,并用筷子扎肉试熟时,我经常跑过去想尽早把握住吃肉的先机,然而即便关火,距离肉吃到嘴儿却还有一段时间——最折磨人的剔肉工序开始了!烀熟的头肉如果不趁热从头骨上取下,一旦肉凉了,便会紧紧粘在头骨上,极难剥离。所以只能趁热,忍住烫手的温度剔取。长辈会安慰馋嘴的孩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却在心中焦虑着暗暗顶嘴:不是说“吃肉要趁热”吗!
其实取下的肉在我家仍属于半成品:猪拱嘴、鼻子,眼睛、金钱(猪巧儿)可以直接切片蘸酱油、蒜泥吃;耳朵可以再用糖烟熏下,然后切丝、切片拌葱丝和黄瓜;猪脸切方块用原汤、酱油扒着吃。扒猪脸这道菜最见手艺:处理不好要么会很油腻,要么太烂没有咬头。同时还要兼顾颜色,红亮而不黑看着才有食欲。这道菜是我奶奶的拿手菜,她做出来的扒猪头肉色泽诱人,很酥很香却不油腻。
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吉林市修建解放东路,永昌胡同平房拆迁,因为新迁入的楼房里不具备使用大锅的条件,加之厨房主力们也渐渐倦于烹饪猪头肉的繁琐辛劳,于是我家的二月二也顺应社会风俗,改为去东市场、新地号、永强市场等处的熟食店购买熟食。可主力们因为省去自己烹饪猪头肉得来的闲暇,并未让节日过得更加充实——或许只有忙里忙外的过程才会营造出节日感,轻易得到的结果反倒让生活的滋味变得寡淡。

图片取自《满族大辞典》
记忆中,二月二吃猪头时还有一些有趣的副产品。在吉林,玩具匮乏的年代,剃下猪的下颌骨是满族儿童的玩具,被叫做卡巴车;猪惊骨,也就是听骨,会被取出洗净,穿上红绳,当作小孩子压惊辟邪之物。我则很喜欢把猪獠牙弄下来,用绳子系成一串,和老公鸡的“蹬儿”(鸡脚增生的角质物,被戴在手指上当作玩具或当做保护铅笔尖的笔套)一起,放在一个有粉色花纹的福源馆馃匣中……
除了吃猪头外,二月二还要剃头。老年间传下的规矩:正月剃头妨舅舅。在过去,正月期间,一般人家都不剃头,吉林城乡老少爷们都在“靠茬儿”(任由头发长长),只等着二月二去理发“剃龙头”。小时候我并不知道这 是汉人“思旧”而沿袭的风俗,却记得当时长辈们说,农历二月二前后就是二十四节气的“惊蛰”,是老龙王在新的一年抬头昂首、行云布雨,催生万物的开始,男人们借机剃头,可以精精神神地开始新一年的工作学习。
小孩子都不爱剃头,多动人的传说也只是传说。我记得自己在二月二,也经常是一百二十个不乐意着去的理发店,由于理发店这天人会很多,排队等候时,我的魂儿经常还被猪头肉撕扯羁绊,莫名其妙地联想:唐长老在高老庄的那个艳阳天里,庄严地为八戒的猪头剃度——理发和猪头都有了,那天应该是二月二吧?
本文为优雅的胡子原创文章,其他自媒体转载须经作者同意。
插图取自互联网,在此向原作者致谢!